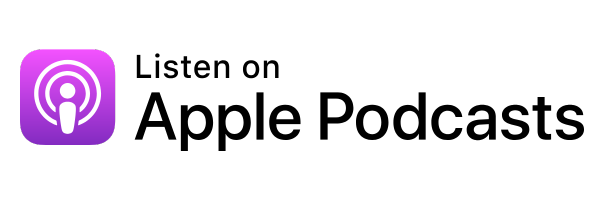庆恩传道讲到的一些东西,我下午还会再展开。
我们教会在过去的这一年多,其实面对各种逼迫的风声和这种压力,上帝带领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多,我们反倒有很多新的事工和一些看见,其实不断地在往前走。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这一年多有很多做法好像很激进,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很保守,所以我们是一个 “末世性的保守主义”的教会。但是如果你保守的是福音中心和教会在上帝整个心意中的中心,其实可以加一个词,叫做“激进的保守主义”。
我想我们稍微有一点时间,在结束之前有一些问题的回答,好吗?待会我们就请几位稍稍有一点对我们的分享有一点反馈,有些问题我可以现在分享,有些也许我在下午讲的时候再回答,好吗?我们就请几位。
提问:王怡牧师,庆恩传道刚刚提到一个问题,讲到说我们教会今天的视野相对于一个“后基督教”的视野,更应该是具有相当多“前基督教”色彩的这种属性。那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的基督教教育观点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以前看您关于古典教育的著作,谈到实际上在我们的古典教育当中有很大程度是一个“守城”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那个东西跟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两种不同的视野,前后有没有变化?对于您个人或您对基督教教育的思考,尤其是在与后基督教的属性相比,我们更具有很多前基督教特征的基督教教育的思考,是不是有变化呢?
牧师回答: 嗯,好,谢谢,很好的问题。我们以前有一次曾经讨论,我曾经讲到,中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和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是有几个非常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当然首先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是在相同上在学习,我们是学生,不是老师。但在另一点上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与教会的处境有关。这个最基本的处境可以说:他们是在一个后基督教的文化环境中,而我们是在一个前基督教的文化环境中。所以有几点:
第一,在美国,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复兴不是一个教会运动的产物。
它家大业大,比如说从60年代以来,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也就是三四十年的时间,在美国的一个复兴,那么在同步的这三四十年当中,美国并没有同步地出现一个与基督教古典教育相应的教会复兴运动。当然也有稍微一点点,就是有人讲说,在美国有一个新加尔文主义的小复兴,包括凯勒牧师、卡森博士、派博牧师,出现了一些新加尔文主义在美国里面的一个小复兴,因为美国在政治上,福音派的右翼在过去三四十年也对美国社会有很大影响,但总的来讲,基督教古典教育在美国并不是一场教会运动的产物,没有同步的一个教会复兴运动。
而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它必须也必然是教会运动的产物,我们强调:没有健康的教会,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教育;没有堂会的建造,没有福音运动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国教会当中的展开,甚至没有过去十年来教会在城市当中的一个公开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刚刚开始的基督教教育运动,包括古典教育的运动。所以今天中国的古典教育运动是高度依赖中国今天发生的这场教会复兴运动,而且必然是这场教会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反过来,它将来也应该成为中国教会运动中的动力。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古典教育中,应当要看见三十年后的中国教会。
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在美国比较重要的两个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学校和学院里面,它的毕业生里面做全职传道人,不只是做牧师,包括其他的全职工作,全职侍奉的比例非常低,大概只有2%,非常非常的低。我们希望在我们人文学院这个比例可以达到20%,到40%更好,我们下午请李英强长老有一些的分享,我们希望我们来推动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在未来的一些年当中可以达到。我在去年他们的开学典礼上讲的道就叫做《十万青年十万兵》,接下来要一寸山河一寸血。所以我们希望今年招生的时候,人文学院的招生广告词就是:“在这里,每个人都进过派出所。”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一年,人文学院学生是百分百地进过派出所,而且有几个姐妹进了三到四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跟教会运动的关系。
第二,与此相应地,不只是跟教会运动的关系,包括跟地方教会的关系。
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基本上是一个超宗派的、跨教会的、缺乏教会背景的运动。但是它总的来讲,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背后的神学的最重要的支撑是改革宗神学,所以在美国它这个运动背后最重要的一些资源、最重要的一些人物还是跟改革宗神学和改革宗教会之间是有很深的关系的。但是,从教育机构来讲,这个运动跟背后的教会之间并没有太深的关系,甚至基本上美国的这一种后基督教的机构完全脱离教会而存在,机构超越教会之外而存在,这是美国总的大画面,它基本上是这个大的画面的一部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不想学它。
所以,第一,我们看到中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是必须与一场教会运动在一起,而且它必然是——第一,它是这个教会运动的产物;第二,它也必须为了这场教会运动而存在。这是跟美国古典教育的不同。
甚至在美国从事基督教古典教育的人当中,都没有“为教会运动而存在”这样非常明显的心,大家总的来讲是扩展上帝的国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更多地,也接下来会是我讲到的再一点就是,他们会更加地强调“文化使命”。虽然我们在中国的处境下会被批评说,你们很多是反对文化使命的人。但实际上,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会更加地强调这些训练出来的人不是教会运动当中的主力,而是在一个所谓的“有机的教会国度”大的国度画面当中,在各行各业,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产生作用的一些基督徒。他们非常强调的是“文化战争”,培养文化战争中能够去打仗的基督徒。当然这场文化战争总体被理解为是国度性的,但是它跟教会运动、与具体宗派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甚至几乎没有很强烈的关系。
那么,我们希望所推动的基督教古典教育是与教会运动在一起,而且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完全脱离地方教会的、不受教会属灵权柄遮盖的一种跨教会机构的教育运动。这是我们与他们之间很大的差别。
同时,我们当然也希望培养能够打文化战争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并不过于地高看,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前基督教”的社会里,我们并不高看,我们并不争取,就是不那么迫切地希望基督徒的子弟出来要进入主流社会,对主流的文化、社会产生影响。我们是希望建立一个基督教自己的文化圈,你明白这意思吗?比如说,很简单,我并不希望看到,我说我不希望,并不是说那样不好,而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当你去追求一个不太可能的目标时,你会丧失焦点,所以我并不太希望看到二十年后,很多基督徒的子弟出来,在各个世俗的公立大学做教授。我并不太希望看到这一点,我也不追求这一点,我希望有一大批的基督教大学中的教授,就是形成基督教自己的学派是第一步。而这一步有可能是半个世纪到一百年都是你的主力,而不是说赶紧训练出来就到这个大学、到那个大学去,然后去影响社会,不要那么强烈地想去影响社会,不要那么强烈地想去占据社会中的文化高地。而是建立自己的社群,建立教会在中国的属灵社群,同时也建立我们的文化社群,建立我们的知识群体。我们只是多元社会中的一员,但是把我们这一员扎根,在中国社会站稳,就是到一定地步,不是要你承认我,我就必须到你那里去,而是我在这边,你稍微……。未来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的转型,最后会完成未来中国社会的,甚至包括政治上的新的立宪制度,那么,在那个新的中国的未来的立宪制度里面,教会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接纳?在多大的程度上,在政教关系的谈判里面,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被接纳?今天的中国政府肯定是不允许、不给我们合法地位的,对吧?不给我们合法地位,我们还是要干。但是未来的中国政府,未来的中国的一个秩序里面会不会允许不受公立国家权力进入和干预的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存在?
其实在今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未来而争的。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有多少知识分子在里面?你有多少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在里面?你有多少是能被别人接纳的?虽然不喜欢你,但是他们也不能说你们是一群笨蛋,也不能说你们这样算什么学问,不能说你们简直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你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能够被接纳的?他们虽然很怪,但这一群怪咖在一起还是有水平的,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被这个社会接纳。甚至在某一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谈判能力,教会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当中的谈判能力。当然我说的这个谈判能力,不是一种世俗的权势的积累,而是你的见证到什么地步,你就在未来的中国制度当中有多大的谈判能力。实际上我们还是在一个前现代、前基督教的里面,前基督教的也就是前现代的。我们先争取的是自己的合法地位,而首先不是占领社会的文化高地,所以这个目标和他们之间有很大不同。
还有一点,美国从事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持有后千禧年中比较乐观的末世论,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在中国呢,至少在我们呢,不是一种乐观的末世论,我们基本还是比较接近中国家庭教会的末世论,即传统的末世论,当然也不是前千的时代论者,而是一种改革宗的无千的,甚至是稍微比较悲观一点的末世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在越来越败坏之中,知道这个社会是越来越糟糕,在整体上是越来越糟糕。甚至在整体上来讲,我们没有这样的包袱,也没有这样的抱负,既没有包袱也没有抱负,就是要求追求一个基督教王国,这个是西方教会的包袱,也是西方教会的抱负。我们既没有这样的包袱,也没有这样的抱负。我们就在一个越来越走向衰落的世界,甚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对基督教、对福音都会有越来越强的抵挡,这个是整个天下大势,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天下大势。
当然不排除在这种大势之中有小幅的升高,对不对?也许在一二百年当中,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会达到一个她有史以来的高峰,这个高峰会不会到在两百年后或三百年后发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高峰会高到什么地步,影响力份额会达到什么地步,也许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也许百分之六十以上,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太认为上帝的心意是要在欧洲的整个基督教世界解体之后要再次带来一个基督教王国的时代。或者很多人说,中国就是接这基督教王国的最后一棒了,中国文化最后会被更新到、扭转到一个地步,就像当年的希腊文化被基督教更新之后一样,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我觉得这是做梦。不信主的中国人也在做这个梦,信了主也在做这个梦。
所以,我们是比较清醒,也不叫悲观,那就不是你的盼望,就不存在悲观。我们是对末世非常乐观的,因为我们对永恒的盼望是如此的乐观,所以我们对现实的这种文化影响力,或者一个文化更新的程度就根本没有那样的指望,也就不存在悲观。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梦做得比我们大一些。我会这样讲,他们的梦做得比我们大一些。所以这个梦做得大一些也会带来里面的焦点,他们也许认为更多的人去做了教授会比更多的人去做牧师可能更好,就是因为他们的梦做得比较大。
至于我们呢,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我们的梦做得更大,所以我们觉得基督教古典教育出来的人更多的人去成为牧师,比更多人的人去成为教授,在中国接下来的几百年当中,都可能是更重要的。是不是永远都是更重要的,我不好说,但至少在接下来的可能一两百年内都是更重要的事。
所以在基督教古典教育的目标上,为基督、为教会,这个不是美国基督教古典教育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当然从无形的国度来讲,它当然也会说它是为教会,但我们是更具体到一个教会运动、一个福音运动来讲,我们更清晰地是为基督、为教会,而且我们的末世观是一种更强烈地将盼望放在永生的末世观。
与此相应的一点是,我们更看重圣经。
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它当然更强调知识的整体性,它强调基督教整个的世界观对所有知识的统摄和更新,但是它会更加强调和它稍微更看重普遍恩惠。圣经作为上帝的特殊启示,在整个教育和知识结构当中的核心地位、中心地位,我认为在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当中不够突出。不是说它不突出,我们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教育,受现代教育影响,圣经在那里更不突出,因为在那里面根本就没有,圣经就几乎已经被拿掉了,与之相比,古典教育是强调这一点的。但是,就我们的看法来讲,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在这方面的强调还不够。
也就是说,中国教会比美国教会更爱圣经。虽然我们以前的爱可能爱得不太有学问,爱得有点愚昧,是一种痴痴的爱,傻傻的爱,也没太搞明白就爱,所以我们希望更聪明地去爱,更合理地去爱,更明白地去爱。但是我们更爱圣经,这一点应该成为中国基督教古典教育,从教育的目标、教育的宗旨,到整个教育的过程、教育的内容上面要更加突出,彰显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圣经真理在整个知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要更加的强烈。
我觉得这几个是我们跟美国基督教古典教育不同的地方,不同是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要更加往前走,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前基督教”的时代。
所以还有一点可能跟他们非常不同,而且甚至是不能简单学习的。我们是一个学生,他们是老师,我们是在学习,但是在某一点上我们是学到方法后要自己来弄的,就是在护教的文化使命。从一个护教的角度来讲,福音对中国文化说话,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不能教我们,他教我们、装备我们去做这件事,但做这件事本身,美国的教会不能教我们。凯勒不能教我们,凯勒让我们看到他怎么在后现代的世俗文化下,去做福音对后现代的文化说话,他在这里面教我们很多的方法,但是福音怎么对中国文化说话,他没有办法教我们,因为那是我们自己要弄的一件事。那么同样,在基督教古典教育当中也是这样子。那么福音作为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对中国文化说话,这件事情是必须要我们自己去完成的,这个任务他不能教我们。
还有一点呢,不仅是说他不能教我们因为他不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是他不能够教我们的,而且在这一点上,甚至在方法上他都不能够教我们太多的,是因为美国的教会,和对美国来讲或者对整个西方来讲,他们的文化已经被基督教浸润了一两千年了。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基督教的世界观跟他们的文化之间,是有同构的关系。既有反的关系,因为这就是后基督教文化的特点,凯勒会在后基督教下面用福音去挑战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大儿子们,对不对?是去挑战这种已经背离了基督教的西方现代文化。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所在的文化跟他们的信仰还是有一个部分是同构的,他反对的是偏离的那一部分对吧?但是它本身是同构的。
但是我们跟中国文化不是同构的,是异质的,质地就不一样,性质就不一样。而这一点来讲的话,是中国教会在今天的教会运动和教育运动都面对的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以福音为中心,在今天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对中国文化说话。
我自己认为说,福音怎么看文化的使命呢?
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福音在人类历史上征服一个文明,使它的文化向他降服,那么过去的所有的例子里面,中国文化是一块还没有啃下来的骨头,而且是两千年教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啃的骨头,因为啃了一千多年。在教会历史上,福音进入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千多年,还没有在这个文化当中取得扎根的,政治上合法的、文化上完全扎根的地位,那除了中国,其实没有第二个例子。从公元635年福音第一次来华到现在,1400年的历史了,那即使新教来华都超过200年的历史了。在其他任何一个人类文明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例子。即使是古希腊、罗马,从1世纪后期到公元313年,也就是200来年的时间,就彻底地降服了那个文化,使得它从文化到政治整个地向福音屈服。那么其他的,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的过程,在任何一个的文明当中都没有经过数百年而不能在其中扎根、不能在其中合法的。只有在中国,它代表着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根深蒂固地抗拒恩典。
而这一块骨头,让我这样讲,福音使命在中国跟文化使命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说,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祂剖析了,祂指责最厉害的,祂用福音去针对、去挑战他们、去揭露他们的本相最多的就是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文化的高峰嘛,犹太人在信仰耶和华,可是骨子里并没有真正地相信祂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的堡垒,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抨击的焦点就是他们,耶稣抨击的焦点是大儿子而不是小儿子,一直都在抨击这个大儿子,最难听的话,都是对他们讲的。但是从某一点来讲,耶稣对法利赛人不是光在骂而已,祂骂得都很到位。耶稣带来了福音对文化的穿透力,耶稣把法利赛人真是讲透了,把他们的罪,把他们的面具真是剥得太漂亮了,太痛快了,就是针针都见血。骨子里面的那些罪,骨子里面的那些伪装,那些假冒为善,不只是说一个字,他在每一件事情上的假冒为善,他是怎么假冒为善,他里面是怎么来包装他自己来抗拒恩典的,在每一个故事里面、每一个预言里面、每一个事例当中,耶稣把他们真是吃透了。
所以,很简单的来讲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把中国人的罪讲透了的应该是教会,对不对?把中国人千百年以来的这种伪装,这种道德的假冒为善,外面的这种面子,里面的那种污秽,那种人际关系当中的诡诈,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很娴熟的一切的伪装全部给他扒下来的。那我问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教会有没有达到淋漓尽致地把这些扒下来?其实没有,也就是说福音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文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穿透力,对吧?把一个儒家的人骂得狗血淋头,而且还骂得针针见血,还骂得就算他不服气,旁边很多人还觉得痛快,这是把他们的要害抓住了。中国教会有达到这样子的地步吗?把共产党里面的贪官,把共产党里面的假道德主义者,这些伪共产党人,这里面他的谎言、他的罪、各种伪装,淋漓尽致地说出来,教会有达到这个吗?把受到现代的西方来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思想,现在中国年轻的一代都是受这种思想影响的,对不对?把这个里面的罪,这个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地剖析出来,教会有达到这一点吗?讲台有达到这样子的力量吗?没有。
所以,福音的穿透力是一定要针对一种文化当中的人和它的罪来发出福音的呼召的,对不对?那这个我称之为福音运动的文化使命,不是一个跟福音运动无关的文化使命。
福音运动的文化使命我觉得在中国是针对两个,第一是针对大儿子,谁呢?就是儒家。中国人在骨子里面都是儒家,假冒为善得不得了,爱面子得不得了,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满嘴的仁义道德,这就是儒家,这就是那个在家里面的大儿子。小儿子呢?小儿子是自由主义,从西方来的,中国传统的道家的思想也有这种,然后加上现代的西方来的。所以福音在中国,要啃这块骨头是要同时对着这个大儿子和对着这个小儿子传扬福音,指出他们的罪来,剖析他们骨子里面的东西。而儒家,法利赛人的背后有谁啊?法利赛人是跟谁结盟的呢?是跟希律和彼拉多结盟的,他的背后有朝廷,自由主义的背后是江湖。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一场新的福音运动必须是带着文化使命的福音运动。今天我们还没有把这些东西说清楚,你要同时向朝廷和江湖传福音,你要同时向着大儿子和小儿子,向着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传福音,你要扒下他们的皮,然后呢?包裹他,然后来向他们传恩典的福音。
所以,我下午会再讲到这一点,中国的教会需要一场新的福音运动。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新的福音运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得更深。既无法在政治上面对一个向你变脸的、打压你的政府,也没有办法在文化上强有力地跟这个国家、社群、文化、城市来建立更深的关系,在那个里面用福音来完成这个挑战。
一千多年没有被福音扭转的这个文化,吃掉它、啃掉它不是一个单单的个人福音工作、个人布道,带他决志信主能够完成的。过去四十年的福音运动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已经达到天花板了。
实际上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对今年所发生的,政府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逼迫,我心中真是觉得是一件好事。我说:主啊,感谢祢!终于来了,再不来中国教会就死定了。
为什么呢?因为它代表一个说,就像中国古代那些江湖上的那些社团、江湖上的那些帮派,如果他们的影响还比较小,它跟朝廷之间还没有太大的冲突。如果江湖上的宗派已经到五千万人了,但是它也不简单是个人数,如果是像白莲教几千万人散在人群当中,信的人没有都在一处,没有对城市构成这种公开性的存在,朝廷也不管他们。朝廷都可以和他们维持一种你好我好,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在过去十几年,政府跟家庭教会已经保持了很长一段睁只眼闭只眼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厉害,对不对?一点小麻烦,睁只眼闭只眼就算了。但是现在呢,人家跟你撕破脸皮了,那就表明人家觉得你们已经发展到我必须要跟你撕破脸皮的地步了。但是你呢?不、不,没有发展撕破脸皮的地步,我们要不退回去一点?别跟我们撕破脸皮,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再隐藏一下。所以,常常政府比你看得准,魔鬼的嗅觉是仅次于圣灵。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一定在魔鬼面前也是个傻子。因为魔鬼的属灵嗅觉是仅次于圣灵的,牠常常已经闻到味道,但教会没有闻到。牠已经闻到硝烟味了,但是教会还想避免,实际上硝烟已经不可避免地起来,也就是说教会在中国已经大到这个地步,已经规模大到这个地步,影响大到这个地步。对中国共产党讲,对儒家加上马列的这个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已经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这是它的表述方式,换一个表述方式就是属灵争战嘛,对不对?它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你不能说它看到的这个是错的,它看得非常准确。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共产党的主体地位已经构成了冲击。这个冲击下去就将“教将不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了,它严重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它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它确实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教会不正面打这一场仗,就不会有下一波的福音运动。无论今天中国教会是七千万、六千万还是八千万,这就是中国教会的“天花板”了。
杨凤岗老师有一个统计,1900年以来或1949以来平均一算,平均年增长最低都是这个数。往前一推,再过三十年,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圣灵的工作,你怎么知道会停在哪一年呢?你明白这意思吧?比如说中国到现在四十年的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年均年增长8%到10%,然后你预测说,再来二三十年就会达到一个什么地步,但是你怎么知道还有三十年呢?因为这个高速增长可能在哪一年,“咔嚓”就没有了,对不对?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四十年,你怎么知道它还会再高速增长二十年呢?福音高速增长也是一样的,圣灵的浪潮,司布真牧师讲,圣灵的工作是一场“阵雨”,下雨的时候你不赶快,下一次就在那个国家下雨了,就在那个城市下了,你这就没雨了。神的恩典是一场阵雨,你不知道,它可能还会再下两个小时,也有可能再过五分钟就没雨了。
所以,如果中国教会没有一场新的福音运动,而这场新的福音运动就会以2018年的这一场逼迫为起点。如果中国教会在这一场中失败,就可能不会有下一波的福音运动。不会有下一波的福音运动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再增长,不意味着我们不会传福音,但是老实说,你看香港和台湾就非常明显,日本就更不用讲了。香港、台湾都经历过教会高速增长的阶段,但是到70年代末之后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台湾这过去的四十年,不是说没有增长,教会都在传福音,大布道会都在做,所有的事情都在做,但是四十年过去了,从人口当中的百分之四、五到现在也就百分之七、八,还是有变化。但是中国过去这四十年可不是从百分之四、五经过四十年到百分之七、八,不是哦,我们是翻了几倍,对不对?翻了几倍。但是随时有可能下来,那有可能就变成香港和台湾这样子的。今天有八千万基督徒,四十年之后呢,我们涨到一亿一千万,那还是很好,对吧?还是很好,但是你就非常知道一件事情,大复兴已经过去了。再过一百年,涨到了一亿六千万,那也是很大的成长,但你知道大复兴已经过去了,那就是常态当中的一个增长,你基本上就是这个点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八千万,有没有可能二三十年后达到一亿五千万甚至两亿,那个就叫做跨一个台阶的增长,那不是一个日常增长。而是跨一个台阶的增长,是福音运动才能带来跨一个台阶的增长,是一个当量,对吧?八千万经过二十年变成一亿,那不是一个当量,你还是在原来那个当量上慢慢有一点涨,但是经过二十年,经过一代人变成两亿,那就是再上一个当量。那各位,中国教会会不会再上一个当量?
2018年显示出来了过去四十年的福音运动的一个尾声。从今年(2018年)教会普遍的回应来看,我认为70年代末开始的这一场福音运动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有些地区的增长,只不过是这场增长当中还剩的红利。很多的教会只是在这个红利当中还是会有增长,但是已经过去了。如果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河南教会、安徽教会遇到今年这样子的逼迫不知道有多奋兴。福音都传遍全国了,随走随传,对不对?出多少坐监狱的,就建立多少间教会。在今年你有看到这个画面吗?河南教会是一败涂地、安徽教会是一败涂地、温州教会是一败涂地、整个中国教会,在整体上是一败涂地。其实,四十年来的福音运动已经停滞了。
甚至从去年的九月宗教条例颁布到今年二月正式执行,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我当然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但是我自己很担心,而且我倾向于认为,在这一年当中,中国基督徒的数量是在减少,而没有增长,是负增长。如果去年九月有八千万,也许已经少了五百万了,很多地方的教会都在停止聚会,很多地方的教会在分散之后不是增长,而是衰退。很多地方的一些基督徒是在放弃信仰,成为挂名基督徒,很多地方的一些教会是在加入三自。家庭教会少掉三百万、两百万、五百万,我认为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神才知道。而且有没有可能这种负增长的局面其实已经持续两三年了,而我们都还并不自知?甚至有可能中国家庭教会在过去两三年,甚至三五年当中已经在开始负增长了。因为在一些城市当中增长的速度低于很多在传统家庭教会地区的衰败的速度和进城之后消散的速度。甚至有没有可能在五六年前是八千万了,现在其实是六千万?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管过去到现在是怎么样,之前我不知道,因为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没有一场新的福音运动的话,八千万就是中国教会的天花板,不会再上一个阶梯了。因为没有一个社会群体可以达到八千万之多,却不与主流社会、主流政治、主流文化发生正面战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到了八千万,还想打“游击战”?那就是自掘坟墓、自毁长城。那就是说嫌多,就是自己已经嫌多了,到了八千万还不打正面战,还不打阵地战,那就是只能死定了。
所以,今天的中国教会缺乏这样子的心,我们不要退,我们现在是要往前走。如果没有一批教会、没有一批城市教会站出来往前走,打一场“阵地战”,这个衰败将会不可阻挡。植堂运动也将中途衰落,因为城市植堂运动是要植堂,堂是什么?我们讲是一个被建立起来的有规有矩的、建制的、一个被联络整齐的教会,这个是过去十年来教会城市化、公开化进程的一个结果,人家现在打的就是这个。所以如果在这一轮当中被打掉了,还会有城市植堂运动吗?不会有了,只有分散小组运动,只有传统的建小组运动,悄悄地建,就是说,还是会有人信主是肯定的,就像在台湾,每间教会每年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福音活动,也每年都会有人信主。但是一场城市植堂运动其实就在2018年被打散了。因为你有的都在往后退,哪来的植堂运动?
那我们就会回到中国教会之前的叫做“被动植堂”——其实不叫植堂,是“被动分散”。而过去的被动分散在总量上至少分散是带来了增长,但是如果在这一轮的逼迫中我们失败的话,“被动分散”有可能不是带来增长,而是带来减少。“义人的根基毁坏了”,你要期待它增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教会在中国已经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就是,你必须向这个世界来见证,必须向君王来见证:耶稣比习近平大,上帝比法老大。这个若不成为教会一个公开、坚定的见证,而且是以受苦的方式、愿意承受代价的方式去见证出来的话,那在中国,基督徒就这么多人了。你没有办法,大儿子和小儿子在整体上都不会信主的。因为在他们那里有偶像,他们那里有最大的,那个最大的没有被拿走,在整体上没有被打碎,那么作为一个“地下社会”、一个“边缘社会”,八千万就是你的顶点。你怎么可能期待有占人口10%—20%的一个社群,却不跟这个社会的主流制度、主流文化之间发生正面冲突?怎么可能呢?那就像鸵鸟一样,埋起头来不看说:“来,咱们增长吧,增长吧。”怎么可能增长呢?增长已经停滞了。这是今天中国教会的现状:增长已经停滞了。
我们今天再说王明道、再说林献羔,老实说,已经不会再是这场福音运动当中的动力了。先贤是先贤,林献羔坐过牢,跟你有什么关系?王明道坐过牢,跟你什么关系?你们不能光吃老本,还在之前的这场福音运动当中,仍然还有一点点的收获了,茶都已经泡了十五遍了。除非这一代人,这一代教会,有自己的司提反出来。除非这一代教会有自己的林献羔、自己的王明道,还有像杨心斐阿姨这样的,就是这一代的牧者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批被上帝兴起的传道人,才会有一场新的福音运动。求主帮助我们。